订阅
|
广州 “爸爸,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。” “我的工作呀,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。” 这是国庆档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的一段对话。 这个在天上写诗的职业就是航天人。而火药雕刻师就是其中一个。 雕刻师是个很浪漫的职业,可是如果前面加上火药2个字,那这个浪漫就要加上引号了。 火药雕刻师的工作是用刀具,手工将多余的固体燃料剔除掉。而在铲除的过程中,不能产生静电,不能出现一点火花,否则就会引起爆炸。 毕竟,对固体燃料进行微整雕刻,是制造火箭固体发动机极其重要的一环,每一刀下去都决定了火箭的路径。 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有这样一场戏,当厂长问有谁可以将固体发动机燃料药面精度操作到0.5毫米,章子怡饰演的火药雕刻师弱弱地举起了手,小声地回答:“我可以做到0.2”。 这位能做到0.2毫米的人物是有原型的。 他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7416厂高级技师、大国工匠——徐立平。 再危险的工作也得有人做 徐立平是个“航二代”。 父母均是我国第一代航天工作者。母亲温荣书是我国从事火药微整形的前辈。 上世纪60年代,国家大搞三线建设,徐立平的父母先后在四川、内蒙、陕西工作。徐立平出生后也随父母几经辗转。 在父母的影响之下,徐立平将老航天人的精神深深刻在了骨子里。 1987年,不到19岁的徐立平技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7416厂固体发动机整形车间从事微雕。 这,也是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。 对于母亲做的这份工作的危险及确切含义,徐立平很快就深切感受到了。 在车间的第一课,师傅让他们在现场看了点火实验。 巨大的爆炸声、窜起的火苗,迎面扑来的热浪以及腾起的蘑菇云,让这群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目瞪口呆。 徐立平备受震撼,原来,母亲一直从事的就是这样伟大的工作啊。而自己今后将要跟随母亲的脚步,与危险同行。 这个岗位到底有多危险呢? 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总设计师侯晓院士曾这样说过:“它就像一个人去擦火柴,他每次必须擦上,但是不能擦出火星。他一旦擦出火星,后果就不堪设想。” 正如章子怡在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演绎的:在车间里,她说话、走路甚至连流汗都是小心翼翼的。每天上班,她都担心自己会回不来。 见到这份工作的“真面目”后,有同学打了退堂鼓。而徐立平却毫不退缩。他相信,只要心存敬畏之心,严格按照规范流程操作,胆大心细,就不会有危险。 徐立平跟着师傅从最基本的拿刀、推刀学起。 在练坏了30多把刀后,徐立平对于下刀的力度、角度以及切削的准度的掌控,达到了一刀准的程度。 在34年的实际操作中,徐立平一直严格按照规定去做。但是再小心,也免不了有意外发生。 那次,可能是刀具不慎碰到了发动机金属壳,瞬间引起发动机剧烈燃烧。车间被烧得面目全非,和徐立平同年进厂的同事当场牺牲。 这是徐立平第一次见到身边熟悉的人因这项工作丢了性命。多年过去,每次提及这次事故,徐立平都不禁哽咽。 但徐立平从没知难而退。 他深知,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药面整形是项世界性难题。 再精密的机器也没有人的手指灵活,有些工作,就必须靠人手的精雕细刻去完成。 而他一直愿意成为这个人,“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子,是一种荣耀。只要这个岗位需要我,我就会一直干下去。” 30余年刀尖上起舞 由于药面整形工作的特殊性,目前,我国从事火药雕刻的人员不超过20人,徐立平就是他们之中的领军人物。 0.5毫米,是国际通用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。 而经徐立平手雕刻出来的药面,误差不超过0.2毫米,那是2张A4纸的厚度,切削下来的药面都可透光。 但这精湛的技艺,是经历了数次磨难才练就的。 徐立平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1岁冒死抢险时的场景。他回忆道“那里面太安静了,除了铲药的声音,只有心跳声在耳边响起,像雷声一样。” 那是1989年,一台火箭发动机在试车前发现燃料面出现裂纹,试车失败,必须拨开填充好的推进剂查找原因。 上级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原地铲药,这是我国固体燃料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挖药,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。 刚参加工作两年的徐立平,毫不犹豫报了名。 当时,发动机内充斥着浓烈刺鼻的推进剂味道,舱内空间狭小逼仄,1米8的徐立平只能用半跪半蹲的姿势,用木铲、铜铲一点一点地抠挖。 在那种高度紧张又缺氧的环境中,时间长了就会头痛、呕吐。因此,每个人一次只能在舱内呆上10分钟,挖上4、5克药。 而徐立平每次都尽量多呆上一段时间。就这样历时2个多月,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公斤的推进剂,找到了故障原因。 这次任务完成后,徐立平有了很严重的后遗症,他的双腿疼得几乎无法行走。那时,他刚结婚一年。 经过很长时间高强度的康复训练,徐立平才能重返工作岗位。但是因为推进剂毒性,他头发掉了许多。还因为常年保持别扭的雕刻姿势,他的肩膀向一侧倾斜,无法纠正。 还有一回,发动机药面脱粘,需要人工用木钻在舱体钻孔寻找药面脱粘部位。钻孔的过程中极易产生静电,执行这项任务的人生死一线。 当时,整个工作区域只留下徐立平和他师傅。 他们用木钻一圈一圈去钻开火药,一分一秒都是生死较量。幸好,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师徒2人完美地完成了这项任务。 作为一名火药雕刻师,徐立平犹如在刀尖上行走,想让“行走之旅”更快、更安全,刀具尤为关键。 为此,徐立平经过多次试验、改进,研发了现在的“立平刀”。 这套半自动整形专业刀具的问世,让徐立平他们的工作效率提高了4倍。 这个全世界最会玩刀的男人,将这项工作做到了极致。 他用100%可靠、100%成功,在火药雕刻师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交出了完美的答卷。 每当看到火箭升空的那一刻,徐立平都为自己的职业自豪。 他刀锋下的成果,见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一次又一次的辉煌。 将时光雕刻成信仰 如今,徐立平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34年,和他同期进厂的同事大多已换岗或离开。 妻子梁远珍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为了我和孩子,你也换到一个安全点的地方去呗。” 徐立平总是回答,再等等。 但这一等就从青葱岁月等到了年过半百。 对梁远珍,徐立平是既愧疚又心疼。 自从梁远珍嫁给他那天起,每天都为他担惊受怕着。 梁远珍曾在采访中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:如果徐立平加班忘记打电话,而她打过去,又一直没人接,她就不放心了。哪怕是在做饭,她都要把火关了,到徐立平工作的地方去看一看,远远地看到他们在加班,心就安了下来。 如果说对于妻子是愧疚、心疼,那对于母亲,徐立平还多了一层遗憾。 徐立平母亲晚年得癌,在医院做手术期间,徐立平因为工作在大山深处,无法亲自照顾。 生为人子,却在母亲最需要他的时候,不能赶到身边。这件事像一块大石头一样,一直压在徐立平心里好多年。 所以,他现在有个心愿,在不忙的时候,能够带着家人出去转转。 除此之外,现在的徐立平仍旧做好微雕工作,只是他更致力于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技术骨干,他将自己所有的经验,编写成教程,毫无保留地教给徒弟。 这些年来,徐立平先后培养出了2个国家级工匠,和无数国家级技师。 让人欣慰的是,徐立平的团队涌现了一批80后、90后,火药雕刻师这个行业有了新的接班人。 在很多人眼里,火药雕刻师的工作是枯燥的、危险的,每一次雕刻都在与死神周旋。 而在徐立平眼里,每一刀下去都是美妙的乐曲,都是在为太空写诗。就像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中的那句台词: “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 火箭是为了自由抛弃自己的东西 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 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” 30余年来,徐立平将时光雕刻成了信仰。他一直记得选择这个行业时母亲对他说的话:“要做,就要做好,做到底”。 这9个字说来简单,但做到很难。 “择一事,终一生”看起来有些无聊,但却有难得的可贵。 徐立平的工作在整个航天领域并不属于高精尖科技,但他就是秉着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专一行、精一行”的工匠精神,不断书写我国固体燃料发动机微雕的传奇。 他让我们看到了平凡的力量,理解了什么是工匠精神。 我想,只要我们能够倾一生的时光与精力、执着与追求,来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,做到完美,做到极致。 那么超越梦想就不会是一句口号。 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徐立平的意义。 .END. 【文|鸢儿】 【编辑|丹尼尔李】 【排版|毛毛雨】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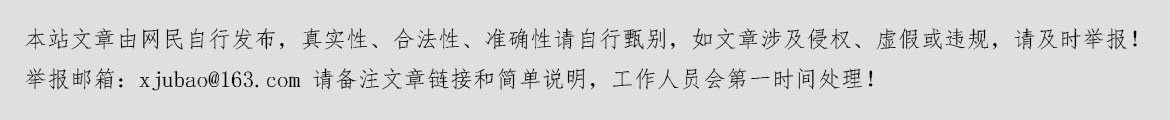
|
|
10 人收藏 |
 鲜花 |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收藏
邀请